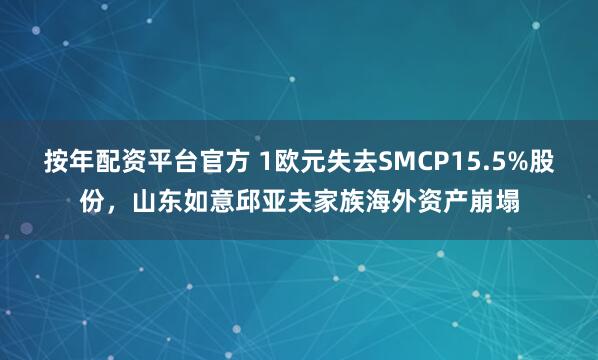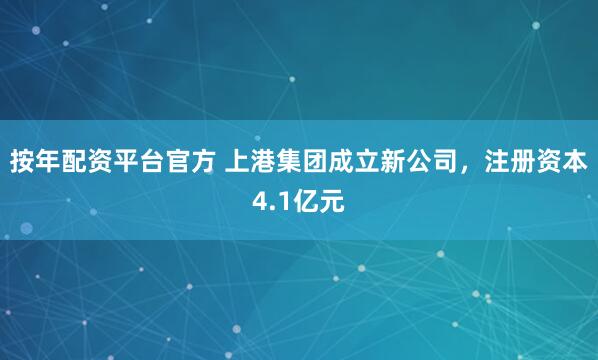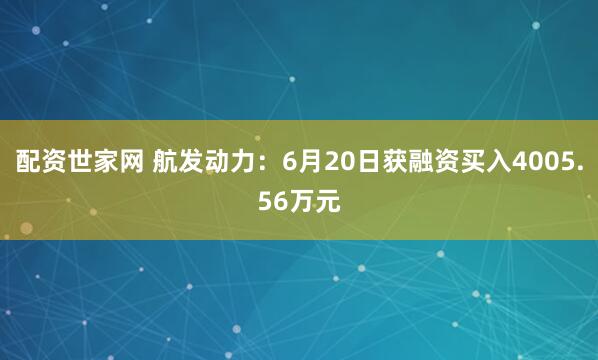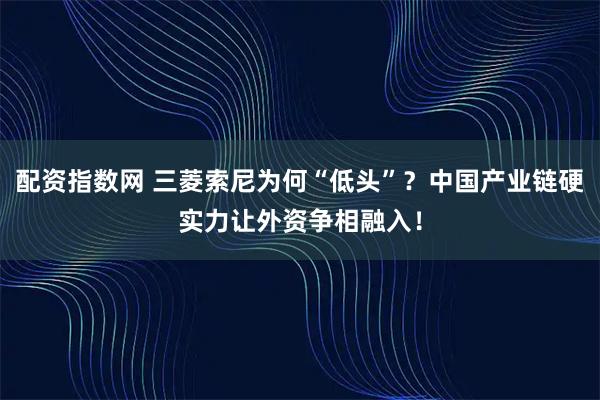一片残阳余晖洒满江面按年配资平台官方,柳枝如丝轻拂,秋风徐来,江上帆影点点,恰似画中景。家国情怀令人悲伤,愁绪无尽,红树青山依旧,却不曾知晓这世间的悲欢离合。
在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一生中,出现了三位重要女性,她们分别是蒋碧薇、孙多慈和廖静文。蒋碧薇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曾如飞蛾扑火般爱上他,却最终以离婚收场;孙多慈是他的学生,两人相恋长达十年,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而廖静文则是徐悲鸿的最后一位妻子。
值得注意的是,蒋碧薇和廖静文都曾为徐悲鸿撰写过回忆录,记录他们之间的点滴,而孙多慈却从未留下任何文字,她的沉默如同那只默默无声的喜鹊,似乎欲言又止,掩藏了太多无奈与痛苦。
在这三位女子中,孙多慈才是最与徐悲鸿心意相通的伴侣,她深懂徐悲鸿的艺术和灵魂,对他的感情也最为深厚。两人不仅在艺术上互相激励,更在精神层面彼此契合。孙多慈本人也是徐悲鸿众多弟子中成就较高的一位。
然而,命运多舛,真挚的爱情并未换来圆满的结局。“慈悲之恋”这段历时十年的感情最终无疾而终。徐悲鸿去世后,孙多慈却做出令人震惊的举动:她在家中素衣素食,守孝三年,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孙多慈,1913年生于安徽寿县,本名孙韵君。她的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要官员,曾任中国首任学务大臣,并创办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她的父亲孙传瑗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秘书,后任大学教授和教务长。孙多慈自幼生长于书香门第,文化氛围浓厚。
展开剩余87%她从小热爱绘画,曾师从国画家阎松父,父亲也教她古典文化,但她对绘画的热忱和天赋尤为突出,家人都戏称她为“小画家”。她顺利从小学到省立第一中学安庆女中,期间画技受老师胡衡一高度赞赏,令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家庭遭遇变故。年仅17岁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因身份被通缉入狱。幸而1930年她高中毕业时,父亲获释。父亲指引她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但未能考取。
孙传瑗便请教文学院教授宗白华,期望引荐孙多慈到女画家潘玉良门下学习。但宗白华对潘玉良并不熟悉,反而推荐她给徐悲鸿,没想到此举开启了一段画坛罕见的旷世奇恋——“慈悲之恋”。
孙多慈开始旁听徐悲鸿的课程。她虽未受系统训练,但凭借天赋,仅用三个月便大有进步,令徐悲鸿赞赏有加。很快,她成为他画中的常客。
徐悲鸿为她绘制了她人生第一幅素描,称赞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或许,只有志趣相投的人,才能心灵相契,触发深层的情感共鸣。
也正是在这时,徐悲鸿对这位十八岁的少女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十八岁的孙多慈正值青春年华,初遇爱情既羞涩又忐忑,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师生关系也开始染上了情愫的色彩。
民国时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师生恋也时有发生,鲁迅与许广平即为一例。徐悲鸿与孙多慈也不知不觉成为其中之一。徐悲鸿坚信这段感情是“天注定”的宿缘,然而不过是偶然的巧合。
彼时,徐悲鸿年近三十五,正值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年华,对爱情无所保留地投入。世人对这段恋情尤为指责,因他已有家室,妻子蒋碧薇曾年轻时与他私奔,育有一双儿女。
或许,艺术家的感情如同画笔下的色彩,浓烈而不羁,徐悲鸿无所顾忌地爱上了孙多慈。1931年,孙多慈正式成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新生,专修素描、美学及古诗等课程,成绩优异,徐悲鸿更是逢人便夸赞她。
然而,绯闻迅速传播,坊间流言纷纷扰扰。徐悲鸿对外不避讳,两人关系愈加亲密,甚至课上只教孙多慈一人,且频频闯入女生宿舍,惹得同学不满。孙多慈无奈之下只得租房居住,并请母亲同住。
1933年徐悲鸿赴欧洲巡展,两人以书信维系感情。归国后重逢,感情更为炽热,甚至被媒体拍到亲吻照片。孙多慈从天目山采下两颗红豆赠与徐悲鸿,徐将其镶嵌于刻有“慈”与“悲”字的金戒指中,象征两人深情。
他们无视世俗眼光,沉浸在彼此的爱与艺术中。徐悲鸿人生中最浓烈的激情便是对孙多慈与书画的热爱。孙多慈常半躺摇椅,静读如猫般安然,徐悲鸿作画时二人书声与画笔声交织,恰似天籁。
徐悲鸿在夕阳下为她绘制《睡猫图》,题诗“寂寞谁与语,昏昏又一年。慈弟存玩。”次年更作《燕燕于飞图》,画中情感深厚。徐悲鸿名作《台城月夜》更描绘了他与孙多慈共处情景,生动体现他们的深情。
然而,这段情感不久便被蒋碧薇知晓。徐悲鸿辩称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却难以令人信服。蒋碧薇回忆,徐悲鸿曾在宴席间偷偷取食糖果橘子送给孙多慈,令她心碎。
对丈夫的背叛,蒋碧薇感到极度失望,她甚至暗中藏起徐准备送给孙多慈的礼物。忍无可忍后,蒋碧薇公开揭发两人绯闻,将《台城月夜》挂在家中最显眼位置以示讽刺,并将孙多慈画像藏匿于佣人箱底。
徐悲鸿在南京建立公馆,孙多慈赠送百棵枫树苗,蒋碧薇怒火中烧,竟将枫树苗付之一炬,徐悲鸿痛心不已,遂将公馆名改为“无枫堂”。“慈悲之恋”虽美好,但终究未被世人接受,结局早已注定。
尽管深爱孙多慈,徐悲鸿仍未放弃对蒋碧薇的道德责任。内心深处矛盾交织,他曾向好友舒新成倾诉心事。好友劝其“台城有路直须走”,希望他勇敢追求真爱。艺术家如徐悲鸿,思维往往与常人不同,情感亦复杂难解。
徐悲鸿的弟子与友人分为两派:一方支持蒋碧薇,指责徐悲鸿背叛;另一方支持徐悲鸿,认为他对孙多慈是真爱。不论如何,徐悲鸿一直保护着孙多慈。
1935年,孙多慈即将毕业,徐悲鸿欲借公款送她赴比利时深造,还为此写了多封委托信。此事却被蒋碧薇破坏,令徐的努力付诸东流。孙多慈无奈回到家乡安庆任教。
两人的感情因此遭受重创,徐悲鸿对蒋碧薇愤恨难平,常闭门苦画,夫妻关系彻底决裂。两人分居两地,徐留在江苏宜兴,蒋去了广西桂林。
徐悲鸿依然挂念孙多慈,频频写信鼓励她坚持画画。1936年,他出资让好友舒新成购买孙多慈的画作,倾注所有心力照顾她。
孙多慈也深知这一切,不仅感恩,更期待有一天能成为徐悲鸿的妻子。但现实残酷,她只能忍耐等待。
三个月后,孙多慈采摘红豆寄给徐悲鸿示意相思,徐感动赋诗《红豆三首》,字里行间充满情感纠缠。
1938年,因战乱,孙多慈一家迁往长沙,徐悲鸿闻讯赶往,将他们接到桂林。尽管战争炮火不断,二人在小小的世界里共享幸福时光。
7月,徐悲鸿公告与蒋碧薇分居,实则离婚。朋友曾试图撮合徐孙婚事,却遭孙父拒绝,孙家迁往丽水,断绝了两人联系。
徐悲鸿悲痛难耐,远赴重庆、印度讲学疗伤,离开数年。孙家漂泊无依,父母将孙多慈许配给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孙多慈为了稳定生活,只得顺从父命。
许绍棣比孙多慈大近
发布于:天津市嘉正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