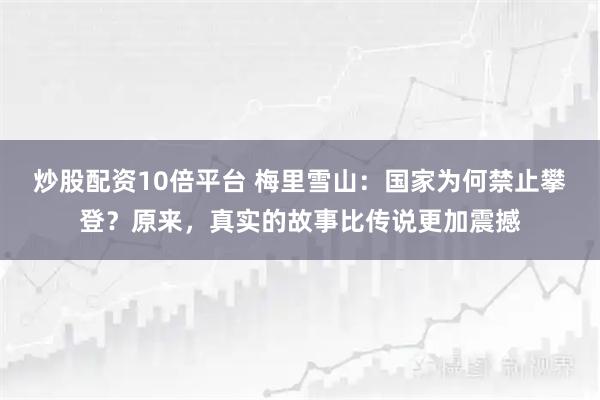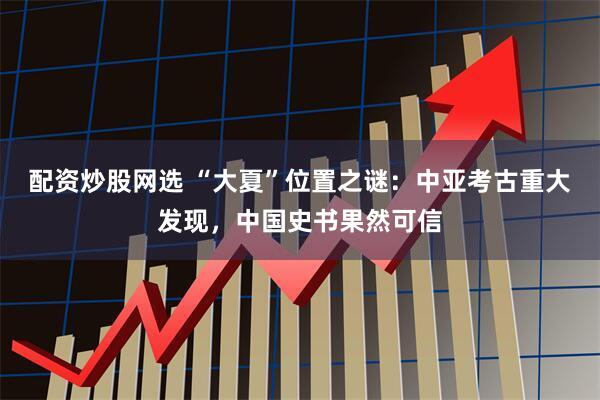
《史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汉时期著名外交家张骞的西域之行。公元前138年配资炒股网选,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主要任务是联络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张骞率领使团穿越河西走廊时不幸被匈奴俘虏,在匈奴境内滞留长达十年之久。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张骞始终牢记使命,最终成功逃脱,继续西行。他先后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撒马尔罕地区)等西域国家,最终抵达大夏地区,找到了西迁至此的大月氏部落。根据《史记》的地理描述,这个被称为大夏的地区应当位于妫水(今阿姆河)以南,即现今阿富汗北部地区,也就是西方学者所称的南巴克特里亚。
关于巴克特里亚这一地理概念,它指的是一个横跨多国的广阔区域:北至兴都库什山脉,南抵西天山,西接帕米尔高原,以阿姆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这片区域涵盖了今天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其中,南巴克特里亚曾是希腊化时期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澎湃新闻刊载的《新丝路学刊》中,王建新教授在《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与中国古代文献存在分歧。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夏并非指南巴克特里亚,而是指由塞克人或吐火罗人建立的政权,同时认为贵霜王朝是由月氏人建立的。
展开剩余80%这一学术争议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按照中国史书《史记》的记载,大夏究竟位于何处?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佐证了中国古代史籍记载的准确性。要探究大夏的位置,必须从大月氏的迁徙路线入手。大月氏原本游牧于中国西部祁连山一带,在匈奴的持续打击下被迫西迁,其迁徙路线从东天山一直延伸到西天山。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公元前129年张骞从匈奴逃脱后,西行数十日抵达大宛,继而经康居最终在大夏找到大月氏。这段记载清晰地表明,从大宛到大夏必须经过康居国境,否则就需要翻越险峻的高山。
值得注意的是,大月氏最初定居在妫水以北,而大夏国位于妫水以南。后来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即征服了大夏国并在此定居。这里提到的妫水就是今天的中亚第一大河阿姆河。中国历代史书对这条河流都有明确而连续的记载。汉代之所以称其为妫水,是因为西迁的大月氏将故土的地名带到了新的居住地。因此,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大夏应当位于阿富汗北部,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核心区域。那么这一记载是否准确呢?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工作为此提供了确凿证据。2020年光明网刊发的《破解大月氏之谜——中乌联合考古的新进展》报道指出,中乌联合考古队取得了两项重要发现:首先,明确了康居的大致范围在撒马尔罕盆地南缘和西天山北麓一带,而大宛则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该盆地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属于康居国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巴克特里亚的广大区域,考古队并未发现任何文化遗存。其次,在现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具有鲜明特征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世纪初期。这些遗存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月氏文化遗存具有高度相似性。这一发现证实,大月氏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已经西迁至北巴克特里亚地区,与中国史书记载的时间节点完全吻合。
根据《史记》记载,大夏位于妫水以南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其东南方向与身毒国(古印度)接壤。而中国考古发现显示,在正对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妫水以北地区,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世纪初期确实是大月氏的统治区域。这些考古证据充分印证了史书的记载,确证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中国史书的记载准确无误。要理解西方学界为何否认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需要考察其背后的学术立场。正如前文所述,西方主流学界坚持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夏并非巴克特里亚。这种观点本质上反映了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因为一旦承认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西方构建的部分古代史体系将面临挑战。
根据《史记》的详细记载,大夏与大宛的风俗习惯十分相似: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司马迁还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些记载或来自张骞的亲身见闻,或来自其他汉使的实地考察。这些文字描述展现的是一个风俗相近、语言相通的文化区域,丝毫不见古希腊文化的痕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居民不知铸钱器,后来是在汉朝逃亡士兵的指导下才学会铸造技术,这说明当地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此外,他们获得金银后首先考虑制作礼器而非钱币,也反映出社会发展水平较为初级。
如果承认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那么根据中国史书的这些记载,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叙述就存在严重问题,进而会动摇亚历山大东征和塞琉古王朝的相关历史叙事。甚至西方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发现的一些所谓古希腊风格遗址和金币(最初宣称是铸造的,后改口为手工锻打而成)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学术界自然不愿承认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的观点,只有将大夏定位在其他地区,才能维护既有的希腊化历史叙事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参与中亚多国联合考古的成果不仅证实了大夏地理位置记载的准确性,同时也验证了《史记》中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的大同俗等记载的真实性,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史籍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反过来说,既然《史记》的记载可信,大夏确实就是巴克特里亚,那么西方历史叙事中关于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相关内容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问题,这为重新审视中亚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发布于:天津市嘉正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